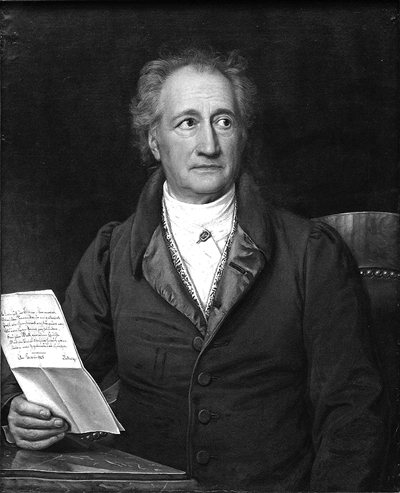
歌德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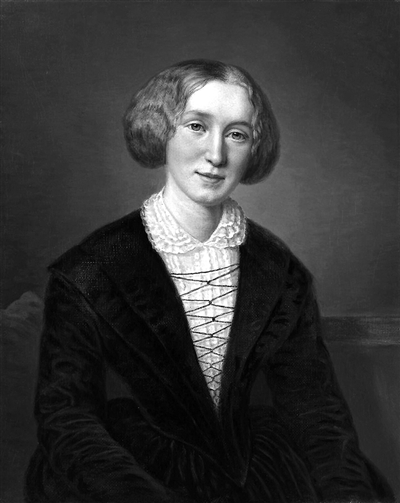
①乔治·艾略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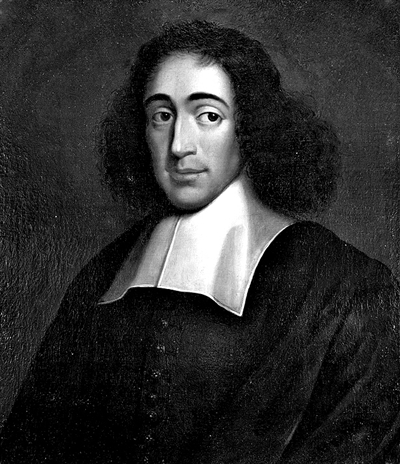
②斯宾诺莎

③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所著《中国近事》
乔治·爱略特是最早被翻译并介绍至中国的英国女作家之一,自1907年至今已经历110余年。1907年,第4期《中国新女界杂志》刊发了国内第一篇有关爱略特的文章,题为《英国小说家爱丽阿脱女士传》,简单介绍了爱略特的生平,在文末对其高度评价说:“爱丽阿脱其人哉,则其可为吾国之人所馨香而顶礼者又岂徒女界宜然哉。”爱略特本人虽从未到访过中国,却并非不了解中国。近百年来,爱略特在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阅读者和研究者。今年正值爱略特200周年诞辰,我们何不从她的作品入手,来解密她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一、爱略特作品中的中国
爱略特与中国,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不容忽视的篇章。爱略特曾在《现代拯救,拯救,拯救》一文中表达了她对中国的关心。该文来自她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西奥弗拉斯特斯·萨奇的印象》中的最后一章,其重要性不容小觑。文中,作者借萨奇之口这样谈中国:
“我没有义务像对待同胞一样对待中国人,但我有义务不用鸦片来毒害他们。我决不以世界主义为借口来毁灭和掠夺他们的劳动成果,并强迫他们接受我的意志。在他们以和平的游客身份出现在伦敦大街上时,我绝不会因为他们服饰和宗教信仰与我相异而侮辱他们。……我们缺乏的就是这种认识:任何别的民族都同样合法地拥有民族情感。我们应该明白,缺乏这种情感,就丧失了最大的福祉。”
主人公的姓,一看就和亚里士多德的得意门生西奥弗拉斯特斯密切相关。后者为古希腊哲学家和植物学家。其所著《人物志》尤为有名,开创了西方“性格速写”的先河。只是在爱略特笔下,西奥弗拉斯特斯不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哲学家,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名字叫“萨奇”的牧师。事实上,“萨奇”这个名字就颇为搞怪,它出于音译,语义相当于中文“某个”,因此西奥弗拉斯特斯·萨奇就是“某个西奥弗拉斯特斯”的意思。可见,爱略特想假借“某西奥弗拉斯特斯”之口,以“性格速写”为文体,通过嬉笑怒骂,对所见所感直抒胸臆。这自然也包括了上述引文中涉及的英国对中国所犯下的一连串暴行: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1860年火烧圆明园,以及侮辱赴英旅行的华人。1868年,英国出台了《药房法案》,正式将鸦片归类为毒品。因此,爱略特在这篇1879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既然英国早在10年前就将鸦片视为毒品,那么,其向中国出口鸦片的目的岂不是为了“毒害”他们吗?爱略特还在文中反复抨击英国对内故步自封,对外却以“世界主义”之名实现帝国扩张的野心,并强调“任何民族都同样合法地拥有民族情感”,以期唤起英国人对其他民族(包括中国人)的同理心。上述严肃的申诉通过“某个西奥弗拉斯特斯”之口道出,在搞笑之余,颇为反讽。
同样严肃的批判也出现在爱略特书信集中。刘易斯(爱略特的爱人)在写给其出版商约翰·布莱克伍德的信中,称他和爱略特正在阅读俄理范的《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东瀛见闻录(1857-1859)》。刘易斯表示,他和爱略特“对英国人在有关中国人的争议中表现出来的对情感和权利的无端漠视,颇有微词”。谈到这个第八代额尔金伯爵(1811—1863),就不得不提他在中国的斑斑劣迹。此人曾历任对华全权专使,《中英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都是其“政绩”。该书作者俄理范曾作为私人秘书陪同额尔金出使中国和日本。他本想歌颂额尔金伯爵的“丰功伟绩”,却一不小心激起了包括爱略特、刘易斯在内的英国知识分子的义愤。
当然,在爱略特的作品中,不乏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猎奇心态。在《知识的看门狗》一文中,通过刻画“彭姆”这个人物,爱略特嘲讽了英国人的文化守旧心态。在书中,西奥弗拉斯特斯打趣彭姆道:“无论我告诉他中国人吃狗肉,澳大利亚鸭子穿毛皮大衣,还是在某些地方人们用吐舌头表示致敬,他都会说:‘就是那么回事,先生’。”彭姆似懂非懂,却不懂装懂,俨然一副将其他文化拒之门外的样子,因此,爱略特称其为“看门狗”。作为其他文化的象征,爱略特举了“中国人爱食狗肉”为例。这就像其他国家的人讲英国菜,一说就是土豆和炸鱼,显然是以偏概全,刻板而又固化。同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中,德隆达的母亲在描述女性困境时,称女人的心必须要小得像“中国妇女的小脚”一样,只有这样,才能专心相夫教子。
事实上,包括爱略特在内的英国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注意到上述刻板印象的局限之处。上文中提到的出版商布莱克伍德曾于1858年5月23日写信给刘易斯,提到了一位即将动身前往中国的畅销书作家艾伯特·史密斯,并认为史密斯此行一定会更新英国同胞对中国的认知。后来史密斯回国后,确实筹备了一场名为“中国”的演出。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俄理范写的游记,还是史密斯的“中国秀”,它们都反映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和想象。在这方面,爱略特也不例外。当然,爱略特对中国的想象还源自其他作品。
二、爱略特中国观的思想来源和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爱略特对中国的想象很可能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中国热”。更确切地说,是源于斯宾诺莎、歌德和卡莱尔的作品。在17和18世纪,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模仿中国的工艺风格,崇尚东方趣味;其二,大量出版传教士的中国游记或回忆录,并翻译中国经典(主要是孔孟哲学);其三,产生了许多假中国人之名,或以想象中的理想中国为对照,讽喻英国时政的作品。这当中,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养料的宝贵源泉之一。
以17世纪近代德国启蒙运动的奠基者斯宾诺莎为例。他与莱布尼茨交往密切,据说两人曾于1676年热烈讨论中国古代哲学。莱布尼茨被德籍华裔学者夏瑞春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166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探讨中国的文章。1697年,《中国近事》出版,里面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通信和文献材料等。受莱布尼茨影响,斯宾诺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宗教思想颇有兴趣,并因此对基督教正统论产生怀疑。值得一提的是,爱略特是斯宾诺莎最重要的两本著作《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的英译者,她称自己的翻译是“对斯宾诺莎生活和思想体系的真实呈现”,这当中自然包括斯宾诺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讨论与思考。
与此同时,与刘易斯的交往也加深了爱略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为了撰写《歌德的生平与作品》,1854年8月2日,刘易斯携爱略特来到魏玛,并在此居住三个多月。同年10月19日,在写给卡莱尔的信中,刘易斯提到他已在魏玛找到大量第一手资料,这当中包括歌德的私人信件。有意思的是,5年后,在爱略特写给威廉·布莱克伍德的信里,她提到歌德早期信件里有一个拼写错误。可见爱略特也曾在两人逗留魏玛时期阅读过歌德的书信。1855年10月,《歌德的生平与作品》出版。在出版前后,爱略特多次向朋友推荐这本传记,还在写给好友亨内尔的信中,称这是一本“充满情感、思想和信息的书”。显然,从收集资料到付梓出版,爱略特始终参与其中,对该书,或者说,对歌德的一生并不陌生。以此看来,爱略特很难不注意到歌德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我们知道,歌德晚年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在1813年11月10日给友人克内贝尔的信里就谈到他已努力读完所有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书。1827年,他还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该组诗最初起名《中国的四季》,里面包括十四首颇具中国格调的抒情诗。
到了19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明显降温,但“切尔西的贤哲”卡莱尔依然孜孜不倦地谈论着中国。他对中国皇帝和思想政治的歌颂散见于他的各类著作中,比如《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与《文明的忧思》。卡莱尔对儒家政治赞誉有加,甚至把中国皇帝比作理想的英雄。爱略特曾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报》上多次发表有关卡莱尔的评论文章,是其最忠实的拥趸之一。当论及卡莱尔时,她直言:“这个时代最出类拔萃或思想最活跃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人不曾受过卡莱尔作品的点化。”她本人也自然包括在内。由此,我们不妨揣测,卡莱尔对中国的热情与谈论也为爱略特对中国的想象提供了渠道。
说到爱略特与中国,还不能不提她对梁实秋的影响。梁实秋(1903-1987)是国内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为爱略特作品的汉译作出过卓越的贡献。1932年,梁实秋翻译的《织工马南传》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他在译本序中写道,“哀利奥特(即爱略特)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恐怕本书还是第一部罢”。实际上,他的译本并非第一部,但他翻译的《织工马南传》确实流传较广,让爱略特迅速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他还表示,自己最赞赏爱略特对人性的描写,就这点而言,爱略特比狄更斯更加深刻。无独有偶,梁实秋又在1945年翻译了爱略特的一则短篇故事《牧师情史》,而在其编著的《英国文学史》中,梁实秋不仅认真评论了爱略特的小说,还数次援引爱略特作品中的段落。有学者认为,梁实秋对爱略特的欣赏,是因为“爱略特在创作时煞费苦心,作品真切表现人生,都符合梁实秋人性论的文学传统”。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正是爱略特作品中所推崇的同情共感能力与中国人的精神格外契合。在《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一书中,辜鸿铭曾指出“典型的中国人给诸位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而这种温良是同情与智慧相结合的产物。他强调中国人的温良源于同情心,而之所以具有这种强大的同情力量,又是因为他们过的完全是“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同样地,“同情”也是爱略特在作品中反复提倡的品质。譬如,在1859年7月5日寄给查尔斯·布雷的信里,爱略特写道:“如果艺术不能引发人类的同情心,它将毫无教育意义。”
同样,正是基于对“同情心”的重视,爱略特才会在百年前为中国发声,而梁实秋才会将她抬到比狄更斯更高的位置。也正是基于对“同情心”的重视,我们值得在爱略特200周年诞辰之际重谈爱略特。
(作者:何畅,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